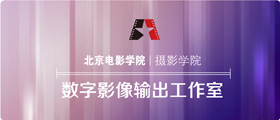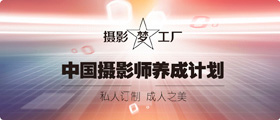| |
|
|
|
|
“不安分”的面点师当上了摄影大师

这回说谁
杨延康
1954年生于贵州安顺,自由摄影师,法国V U图片社签约摄影师。杨延康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纪实摄影师之一。曾工作、生活于深圳多年,分别于2005年、2009年两度获德国“亨利·南恩”HENRINANNENPREIS摄影大奖;三次获得“中国最有影响力摄影人物”;2002年获韩国东江首届国际摄影节最佳外国摄影师大奖;2007年获首届沙飞摄影奖,作品50幅被广东美术馆收藏;2012年获徐肖冰典藏大奖 。
1984年来到深圳时,杨延康还没碰过相机,他是一位面点师,在食堂给工人们做早餐。后来他被《现代摄影》杂志主编李媚招入杂志社做发行,受李媚及《现代摄影》氛围的影响,走向摄影之路。2014年他从深圳搬到了成都。近日他返回深圳参加国际城区影像节,为公众导览卡帕,也讲述自己的摄影人生,同时受邀参与国际城区影像节公众单元“城市与我”影像计划的拍摄。
他的起点
那时的“青年面点师”是个文学青年
“1984年我来到深圳,感谢这个城市对我的包容、宽厚和接纳。从深圳《现代摄影》杂志开始,我认识了摄影,找到自己的信仰和归宿。在《现代摄影》杂志工作,我的老师是李媚,李媚老师是我的恩师,她让我认识了纪实摄影的真谛。”
8月30日,著名纪实摄影师杨延康回到深圳,出现在深圳大学美术馆“聚焦与失焦———罗伯特·卡帕影像回顾展”上,他为公众进行了一场生动的导览。随后,他转移到深圳中心书城“我与玛格南”现场,带来一场《纪实的力量》的主题讲座。他以感恩的方式开始自己的演讲,上面就是他发自内心的开场白。
但其实,杨延康来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,并不是在《现代摄影》杂志社做发行,而是在深大附近的一个酒家给人做早点。当年在贵州安顺老家因为遇到基建工程兵,听说深圳,产生向往,就在贵州的一个酒店报名学厨艺、做面点,学了一个月,参加当时深圳南头抚顺公司的招工考试,竟然考上了。
“1984年12月30日,跟着一辆拉厨具的货车来到深圳,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,刻骨铭心。”杨延康对南都记者说。
做为面点师的杨延康,当年其实是一位文学青年,在安顺时曾听过李媚讲课,那时李媚是安顺文化馆的馆员,巧的是,李媚也来到了深圳,并且去到杨延康所在的公司看望一位朋友。做了两个月面点师的杨延康心里不安分起来,就跟李媚说自己喜欢摄影,问杂志社要不要人。杂志社正好缺一名发行人员,就这样杨延康进了《现代摄影》。
“我没有摄影的背景,也没有学过摄影,是我的导师李媚让我从一张张照片,从来稿里拿出来,看看照片,你哪个喜欢,哪个不喜欢,为什么喜欢,为什么不喜欢,从而认识了摄影。”杨延康说。1992年,杨延康离开了《现代摄影》杂志,要做一个自由摄影师。“我觉得我独立了,我不受雇于某一个媒体或者机构,我可以独立地去践行,去拍照。所以我十年西藏,一年有八个月,四个月去西藏拍照,两个月回到深圳,在工作室里面,把胶片冲出来。四个月又开始去拍照了。我觉得自己一个人,虽然孤独,但我不孤单。我生命中充满了很多力量,一直往前践行,不断地行走。拍摄让我感激有信仰的人,每一个有信仰的人,他的眼睛是温和的,内心是坚定的。虽然碰到一些人为的困难,他会自己去克服。唯有信仰是幸福的,我找到这个信仰的源泉,支撑我纪实摄影的坚定的力量。”杨延康说。
他的路
用商业摄影支撑纪实摄影
杨延康自己买的第一台相机是尼康FM 2,这是当年卡帕在战地上用的同款相机。谈起卡帕,谈起玛格南,杨延康始终感受到一种被鼓舞的力量。
他说,“今年是玛格南图片社成立70周年,玛格南是我们摄影师的神,是我们的坐标,是我们追求的精神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图片社。我们以玛格南的每一个摄影师作为我们拍摄工作前行的坐标。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深圳大学美术馆导览罗伯特·卡帕的作品。63年了,一个生命结束了,战地摄影师,我们的卡帕,能让大家记住他,是为什么?这就是他的照片,这就是他的精神,然而延续了他的生命。我也非常感谢大乾艺术,能够把这么优秀的玛格南的作品带到深圳来,让深圳人能亲眼亲历,罗伯特·卡帕的回顾展非常重要,大家应该看这个展览,不但应该看,还要传播出去让更多朋友来看。玛格南的精神,特别是对我一个纪实摄影师,这么多年低头、谦卑践行的行走,起到很多内在的作用。”
从杨延康对卡帕与玛格南的谈论,不难发现他的精神原动力就来自这些纪实摄影的大师,来自纪实摄影本身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照。
“卡帕关于战争的照片,没有拍大量的死亡和血腥,拍的是人性和爱。他的照片更多是温情,是苦难中人性的东西。”
“我觉得我的信仰,是从苦难开始的。为什么要拍这种苦难?他们的悲悯之歌,他们的命运,包括那些麻风病老人(1998-1999年,他拍了麻风病康复村的系列影像《悲悯的歌》)。1998年到现在好多老人都去世了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精神留给我了,苦难建立了我的信仰。”杨延康说。
然而支撑着杨延康的信仰是商业摄影,他需要在深圳拍商业广告来挣生活费、胶卷费。
“因为深圳这个城市,它不相信眼泪的。我拍过商业广告,拍过王石,拍过任克雷,拍过马蔚华,他们给我几千块钱。我跟我的助手交了房租,领了工资,就可以买胶卷,背着相机就出发了,就去到陕北。”杨延康说。
采写:南都记者 谢湘南
他的回顾
“感谢深圳这个城市的厚爱”
9月2日,记者来到罗湖越众文化产业园杨延康的临时居所,一个单间,这两年回深圳,他都会住在这里。谈起为什么搬离深圳,杨延康直言,因为深圳生活成本高,压力大。他在深圳生活30年,出行都是坐公交车,其实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很低,生活很简单,内心要求的就是精神生活。“十年,你是为了生存,二十年你还是为生存,三十年你还在谈生存问题,谈焦虑。你到底在 这 个 城 市 得 到 什么。”杨延康表示,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遵循内心的需要。现在回到深圳,参与“城市与我”的拍摄,也会常回来做工作坊,他很感谢这个城市的厚爱。
杨延康离开《现代摄影》杂志后,曾注册过一个工作室,叫“真实影像”,除了他提到的深圳商业大鳄,他其实拍得更多的是产品,还有艺术家的作品。他的第一单商业广告是拍一部电话机,当时不知如何拍,拍一个产品要费时半天。他的工作室从最初的桂园路,搬至红荔路,最后搬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。但在华侨城文化创意园内的空间,朋友无偿给他使用,零成本用了7年,谈起这一点,杨延康同样是充满感激。
“我觉得一个摄影师一定要不断践行,不断去路上拍照片。有信仰的人懂得感恩、懂得敬畏。”杨延康说。
“我觉得深圳宽容,也开放。如果你们手中有一台相机,思考一下相机该拍什么。”在讲座现场,他面对摄影爱好者提出了自己的期待。
来源:中国摄影在线